但不是每一桩悲剧,都能碰到讲故事的人。
以灵异鬼怪为主题的恐怖文艺作品,向来难做到广义上的「讨喜」。大家熟知的那些经典恐怖片,票房不说,就连评分都不算很高,因此圈内有「恐怖片 6 分以上就是好片」的说法。《午夜凶铃》和《咒怨》在豆瓣上的评分都是 7.4,而强如《闪灵》,也是 8.1 分——已经是奇迹般的高分。相比之下,同门兄弟「惊悚电影」,则更容易得到大众的高分。
游戏圈也一样。虽然因为上手门槛天然比电影高,使得恐怖游戏的评分环境比电影友好一些,但这些年也是在逐年紧缩。曾经的经典恐怖游戏系列几乎都没了下文,《零》和《寂静岭》系列很久没有新作,只有《生化危机》一枝独秀——还是这里面恐怖要素最少的那个。现在恐怖游戏玩家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一些大众圈子完全没听过的中小游戏。
这个局面不难理解,惊吓本身总归不是让人舒服的事情,这决定了恐怖作品的小众属性。不然你可以问问自己和朋友,听说过那么多恐怖电影和游戏,真正完整体验过几部?然而心怀恐惧的你,却兴致勃勃地看完了《还愿》的故事,并且在网络上爬别人的深入分析贴。《还愿》是个恐怖游戏,也是个特例。它少见地火出了圈外,发售短短几天,就连和游戏没什么关系的号都开始聊这款游戏,而一线的直播和视频网站,更是集体被这股热潮淹没。
《还愿》讲好了一个恐怖故事。更重要的是,它把这个故事传达给了大众——那些原本不会去主动接触恐怖游戏的普通人。
这是如何办到的?
( 下文含有部分《还愿》剧透,但不会比你在社交网络上看到的边角料更多。)
一
在「赤烛」这个名字尚未诞生的时候,《返校》还是一个完全架空的故事。
《返校》的雏形叫《魔都》,灵感来自《1984》,制作人姚舜庭虚构了一个阴森森的极权社会,想做一个小人物在其中挣扎的游戏。
埋头做了一年,姚舜庭差不多用光了存款,游戏的 demo 几近失败。他在 Facebook 上和朋友聊天,把游戏截图发了过去。朋友很惊讶,「我很喜欢你的风格,配合台湾的校园鬼故事,感觉可以做一个作品」。
这个朋友和鈊象电子合作过,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制作人。随着他的入伙,这个游戏一直做了下去,《返校》诞生了。游戏发售后,很多当地媒体用这样评价:「他们用电玩说台湾故事」、「用在地元素反攻全世界」,《返校》成了台湾本地文化输出的代表。
为了年轻人的选票,台湾的政客是很「跟风」的。民进党「立委」陈其迈在 Facebook 上称赞《返校》,说它能够通过游戏「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台湾,并让更多年轻一辈的人了解到过去白色恐怖的台湾共同的痛」。去年《返校》宣布改编成电影,还有台湾文化部门的官员专门站台宣传,讲「说别人的故事不一定赢,但说我们的故事一定可以贏別人」。
绿营政客们话说得太满,自然被两岸网友批评说用游戏当「政治炮弹」。
现在上 B 站看《返校》的视频,还有不少弹幕能因为这些事吵起来。不过,游戏的背景故事年代久远,加上地缘隔阂,种种争论,都仿佛隔靴搔痒。
二
其实按赤烛的说法,《返校》没有「故意挑敏感的白色恐怖当背景」。他们只是觉得,台湾人一听到「戒严」或者「白色恐怖」之类的关键字,心底就会有一股压迫感油然而生。戒严时期的那些符号和意象,拿来做恐怖故事的元素最合适不过了。
到了《还愿》,故事背景就完全去政治化了。但符号和意象,还是取自台湾的闽南文化背景。台湾闽南人的祖籍以漳州、泉州居多,当他们的祖先跨海迁徙到台湾时,带去了闽省的方言,也带去了和语言符号一体的宗族和信仰体系。我的一位闽南同事在玩《还愿》时就完全没有恐惧感,反而觉得有些亲切。
闽南文化里,人和神与鬼都生活在一个想象中的共同空间中。人在敬神的时候,更像是在处理好人和人的关系。这也可以从台湾闽南人对鬼神的称谓中看出来:观世音菩萨是「观音妈」,玉皇大帝是「天公」,天后娘娘是「妈祖」或「娘妈」,都是对长辈的称呼。对神如对人,就萌生了很多更地方化、功能化的神灵。敬畏之外,也就有了猜忌和贿赂。《还愿》里杜家供奉的神,不熟悉的人可能会以为是常见的关公,其实是地方戏曲神「田都元帅」。直到杜丰于请了慈孤观音进来,田都元帅还是供在慈孤观音头上,足见他对自己编剧事业的重视。
观落阴也不是什么已经被革除的陋习,现在还有所谓的「观落阴旅行团」,号称在灵媒带领下能够去阴间一日游。1997 年,台湾艺人白冰冰的女儿遭绑匪劫持,发生了震惊全台的「白晓燕命案」。女儿死后,白冰冰找遍了全台湾的神祠宗庙,希望能够通过观落阴再见女儿。二十年过去,靡费千万,白冰冰还是没有看见女儿的影子。寻女无果,她对媒体说,自己被神棍骗了。这是《还愿》里何老师行骗的十几年后还在发生的事情。
病急乱投医、逢庙就烧香,一些本地的文化元素,莫过如此。
三
人民日报去年发过一篇文章,叫《用精品游戏讲好中国故事》,里面说:
「虽然中国已成为游戏输出大国,但游戏类型较为单一,一些游戏还处于模仿美、欧、日、韩模式的阶段,对中国故事的讲述以元素符号居多。未来,国内游戏厂商应……用更为内在、更为柔性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刨除「元素符号」,中国故事剩下的是什么?
同样是官媒,光明日报有篇《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游戏该登场了》时举例,中国元素是「 水墨丹青、汉唐衣冠、梅兰竹菊 」。这种「中国风」很常见,但似乎有些刻板化。去年这些讲传统文化的游戏很多,从《尼山萨满》到《绘真·妙笔千山》,都做得很美。
美到和现实有一层隔阂。梅兰竹菊的「中国风」是永恒的,但却没几个中国人是在梅兰竹菊和水墨丹青里长大的,每个人切身经历的,是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时代文化。八九十年代的惊悚灵异元素,在闽南是明牌、邪神和观落阴。如果到了东北,大概会变成窖藏白菜和下岗潮。上个星期,高雄市长韩国瑜给一场产业论坛致辞,说台湾过去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整整鬼混二十多年,完全在退步,让人想到都无法接受」。其实台湾从未成为「四小龙」之首,但这并不妨碍台湾人怀念那段黄金年代。就像台湾作家杨渡在《一百年漂泊》里写的,从六十年代开始,「似乎全台湾都做了发财梦」,《还愿》的男主杜丰于的梦,也不过如此。杜父其实是一个相当脸谱化的角色:大男子主义、不希望身为明星的妻子抛头露面;做着过气编剧的成功梦,不能容忍自己的失败;望女成凤,为美心做所有自己觉得好的事,买所有能买的昂贵的东西——红龙鱼、拍立得,还有那架雅马哈的钢琴。
与其说杜父失心疯是为了财,倒不如说是他不能接受穷困潦倒让自己失了面子。所以他才会在越穷的时候,更要买越贵的东西。杜父的心魔,是一个在黄金年代里却没有黄金的人的心慌。这样的父亲,随便哪栋居民楼塌了都能压到一大片。不过大多数人身边的家庭悲剧,只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没有到人亡那一步。杨渡在《一百年漂泊》里还写道,「后来我才真正地了解,一个经济学上的小数点,一个零点零几的农工经济的增减,都可能是无数家族的流浪迁徙,辗转漂泊,无数孩子命运的上升,或者沉沦。」
《还愿》里杜家的悲剧,也不过是台湾辗转历史中一个沉沦的小数点罢了。没什么轰轰烈烈的地方,不是瞬间的洪流,从 1980 年搬进新家开始,到 1985 年、86 年……一切寂静、悄悄地转变着。到最后,「迷信」成为了毁灭掉这个家的直接原因,故事结束了。
四
讲故事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
赤烛和乐队「草东没有派对」合作完成了《还愿》的同名主题曲。说起来奇怪,草东是一支舞曲风格的摇滚乐队,乍一看和「中式恐怖」完全不搭。但到了游戏里,主角推开卫生间房门的时候,「还想和你谈论宇宙和天空/或是沙滩里的碎石和人生」的歌词唱起,却让人刷刷刷地流下了眼泪。
让人忍不住落泪的,还有那首动听的《码头姑娘》。
赤烛的联合创始人杨适维写下了这首曲子。杨适维年轻时在迷幻摇滚乐团「南瓜妮歌迷俱乐部」当过键盘手,也在三菱日商银行担任过储备干部、按部就班当过上班族。但这一切都让他感到空虚,最后他选择放弃了高薪的工作,拿出积蓄入股赤烛,从零开始学习怎么做游戏。
草东有首歌叫《等》,是这样唱的:「我在等的那部车呢/它会不会又抛锚了/我在等的那个人呢/他会不会又不来了」
「等」不是重点,「又」才是重点。
不论是草东还是赤烛的成员们,这些生于八九十年代的青年,在解严的台湾度过了自己最青春的岁月。他们的青少年在蓝绿二元之争里渡过,闷头熬过大考,上了大学后才发现,学历并没有给他们未来——那些父辈原本允诺过的东西。台湾有乐评人说草东的第一张专辑《丑奴儿》是「鲁蛇(Loser)世代的身份证」,草东的主唱巫堵接受采访时却说,「我们不想了解你们定义的鲁蛇」。
姚舜庭在《返校》做完后接受媒体采访,也说「台湾人的眼睛被蒙住了,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就好像父亲从来不会解释除了读书人还能做什么,不做公务员还能做什么。」这些被定义的过去,构成了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愿》里八十年代的台湾家庭,不外如此:美心必须要做大明星,巩莉芳必须要相夫教子,杜丰于必须要重新飞黄腾达,成为大作家大编剧。偌大一个家庭,甚至没有选择退步和放弃的权利。
这样的故事内核,与恐怖无关。
你可以看到《还愿》虽然火热,但社交网络上关心游戏里的 Jumpscare 和鬼魅身影的人,却是少数。
微博上讨论的最多的,除了「阿嬷家模拟器」、杜家房子的户型和风水好不好、郁金香怎么叠,是杜家一家三口的跌宕命运:巩莉芳下落如何?杜父到底爱不爱美心?到底是邪教错了还是杜父错了?说到底,《还愿》不是关于「迷信」的,而是关于「心病」的。「迷信」是宗教元素的恐怖表皮,但「心病」,才是故事的根本原因。它之所以能火出游戏圈,大概还是因为从外表到内核,都是在讲一桩完整的、中国人都懂的家庭悲剧。假如杜父没有遇到慈孤观音,也会找遍其他门路,追求东山再起。就算美心没有遭遇横祸,也会在杜父铁腕式的家庭管教下成长。
信邪教的杜父可笑吗?按邪教的方法试图「拯救」孩子,「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是其实是最寻常的中国故事,我们每个人都听说过:
但不是每一桩悲剧,都能碰到讲故事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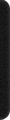








 Alca
Alca Amber
Amber Belleve Invis
Belleve Invis Chensiting123
Chensiting123 Edward_mj
Edward_mj Fotile96
Fotile96 Hlworld
Hlworld Kuangbin
Kuangbin Liyaos
Liyaos Lwins
Lwins LYPenny
LYPenny Mato 完整版
Mato 完整版 Mikeni2006
Mikeni2006 Mzry
Mzry Nagatsuki
Nagatsuki Neko13
Neko13 Oneplus
Oneplus Rukata
Rukata Seter
Seter Sevenkplus
Sevenkplus Sevenzero
Sevenzero Shirleycrow
Shirleycrow Vfleaking
Vfleaking wangzhpp
wangzhpp Watashi
Watashi WJMZBMR
WJMZBMR Wywcgs
Wywcgs XadillaX
XadillaX Yangzhe
Yangzhe 三途川玉子
三途川玉子 About.me
About.me Vijos
Vijos
